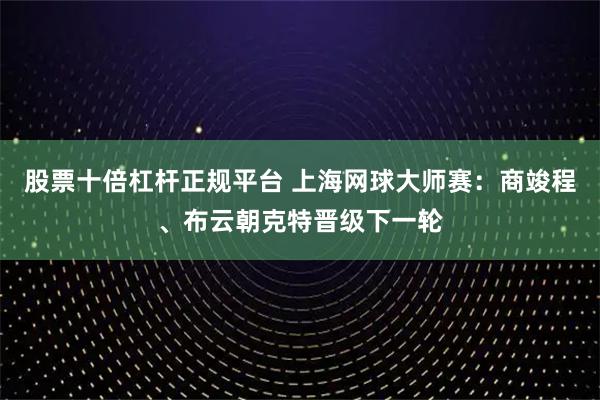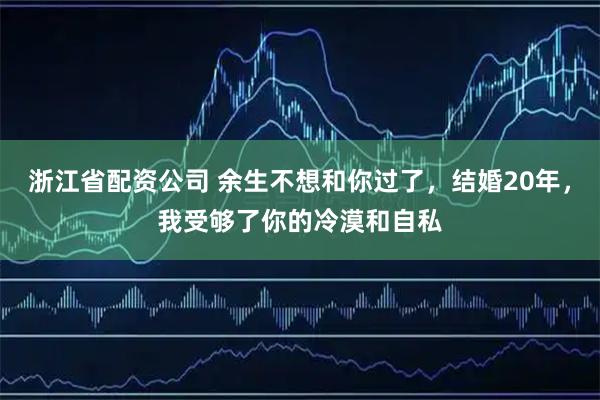
 凌晨三点,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泛黄的水渍发呆。旁边老周的呼噜声像台破旧的鼓风机,一下下捶打着我的耳膜。结婚二十年,这声音从陌生到熟悉,如今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床头柜上放着他昨天换下的袜子,团成一团扔在充电器旁边,就像这个家在他心里的位置——用完即弃,从不在意。
上个月女儿生日,我提前半个月订了餐厅浙江省配资公司,反复提醒他那天早点回家。结果他还是在酒桌上被客户灌到深夜,回来时领带歪在脖子上,身上混着烟酒味倒头就睡。女儿抱着没吹完的蜡烛坐在沙发上哭,我蹲下来给她擦眼泪,才发现自己的手也在抖。冰箱里还冻着去年结婚纪念日的蛋糕,他当时说项目忙,转头却在朋友圈晒出和同事的庆功宴照片。
最让我心寒的是去年冬天我急性阑尾炎手术。麻醉醒来看见的不是他,护士说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,留了句“公司有急事”。我自己举着吊瓶去卫生间,输液管扯得手背生疼。同病房的阿姨叹着气帮我倒热水,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忙吗?我只能尴尬地笑,心里却像被冰锥扎着——他不是忙,他只是觉得我没那么重要。
这些年我像个陀螺围着他转。他爱吃的红烧肉要炖够四十分钟,衬衫必须熨出笔挺的折线,连他母亲的降压药都是我按月备好。可他呢?我的生日永远记成阴历,说“反正都是同一天”;我随口提的想看画展,转头就被他“那有什么意思”堵回来;甚至连我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,他扫一眼就丢在桌上,说“人到中年谁没点小毛病”。
昨天整理旧物时翻出个铁盒子,里面是刚结婚时的信。他那时在信里写“要让你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”,字迹被水洇开了一小块,像我此刻的心情。女儿突然从背后抱住我:“妈,你最近是不是不开心?”我摸着她的头,突然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时,他正对着手机刷股票。“又闹什么脾气?”他头也没抬。我把二十年的隐忍压成平静的声音:“这不是脾气,是决定。”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,在他错愕的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我站起身,终于不用再为谁熨烫衬衫,不用再记谁的口味,不用在深夜听着呼噜声睁到天亮。
走到楼下时,风掀起我的衣角。手机震了震,是女儿发来的消息:“妈,我支持你。”抬头看见两只麻雀在树枝上打架,扑棱棱的翅膀搅碎了晨光。原来离开一个消耗你的人,空气都是甜的。
凌晨三点,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泛黄的水渍发呆。旁边老周的呼噜声像台破旧的鼓风机,一下下捶打着我的耳膜。结婚二十年,这声音从陌生到熟悉,如今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床头柜上放着他昨天换下的袜子,团成一团扔在充电器旁边,就像这个家在他心里的位置——用完即弃,从不在意。
上个月女儿生日,我提前半个月订了餐厅浙江省配资公司,反复提醒他那天早点回家。结果他还是在酒桌上被客户灌到深夜,回来时领带歪在脖子上,身上混着烟酒味倒头就睡。女儿抱着没吹完的蜡烛坐在沙发上哭,我蹲下来给她擦眼泪,才发现自己的手也在抖。冰箱里还冻着去年结婚纪念日的蛋糕,他当时说项目忙,转头却在朋友圈晒出和同事的庆功宴照片。
最让我心寒的是去年冬天我急性阑尾炎手术。麻醉醒来看见的不是他,护士说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,留了句“公司有急事”。我自己举着吊瓶去卫生间,输液管扯得手背生疼。同病房的阿姨叹着气帮我倒热水,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忙吗?我只能尴尬地笑,心里却像被冰锥扎着——他不是忙,他只是觉得我没那么重要。
这些年我像个陀螺围着他转。他爱吃的红烧肉要炖够四十分钟,衬衫必须熨出笔挺的折线,连他母亲的降压药都是我按月备好。可他呢?我的生日永远记成阴历,说“反正都是同一天”;我随口提的想看画展,转头就被他“那有什么意思”堵回来;甚至连我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,他扫一眼就丢在桌上,说“人到中年谁没点小毛病”。
昨天整理旧物时翻出个铁盒子,里面是刚结婚时的信。他那时在信里写“要让你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”,字迹被水洇开了一小块,像我此刻的心情。女儿突然从背后抱住我:“妈,你最近是不是不开心?”我摸着她的头,突然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时,他正对着手机刷股票。“又闹什么脾气?”他头也没抬。我把二十年的隐忍压成平静的声音:“这不是脾气,是决定。”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,在他错愕的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我站起身,终于不用再为谁熨烫衬衫,不用再记谁的口味,不用在深夜听着呼噜声睁到天亮。
走到楼下时,风掀起我的衣角。手机震了震,是女儿发来的消息:“妈,我支持你。”抬头看见两只麻雀在树枝上打架,扑棱棱的翅膀搅碎了晨光。原来离开一个消耗你的人,空气都是甜的。
同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